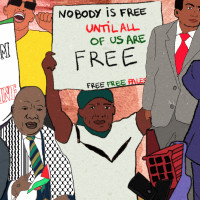Illustration by Fourate Chahal El Rekaby
在“革命外交的历史惯性”与“以经贸关系为中心的当下诉求”之间: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外交政策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文化大革命以一场突然的政变告终。在这场政变中,中共内部保守的温和派别强行镇压了极左派别的领导人,后者则在后来的官方文献中被贬义地称为“四人帮”。作为改革派领袖,邓小平用了两年时间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权力。1978年,邓小平成功召开了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序幕。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与埃塞俄比亚领导人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的谈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的指导方针将从此“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1988)。
在外交层面,这一转变意味着支持全球革命不再是中国官方外交的议程。到1980年初,邓小平已经停止了中国对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南欧共产主义政党与武装组织的援助。随着中国试图吸引西方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球范围内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项目在中国外交政策中也逐渐被边缘化。中国开始重新考虑与更多资本主义阵营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以色列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转变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埃以关系的改善使得中国相信,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或许已经趋于落幕。基于这种认知,1980年7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公开宣布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新立场是“中东各国应该普遍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这一声明标志着中国结束了20世纪60至70年代支持巴勒斯坦人通过武装斗争摧毁锡安主义政权的固有外交立场。中国开始认为以色列国的存在与巴勒斯坦国的存在并不对立。 1982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向约旦国王侯赛因建议,阿拉伯国家应该加强团结,“以色列在中东地区侵略扩张造成的恶果一定要清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和尊严必须得到恢复,同时也承认以色列人民享有和平生存的权利。”。同月,中国总理赵紫阳访问埃及时再次宣布,只要以色列“撤出所占领的阿拉伯土地”和“恢复巴勒斯坦人重建国家的合法权利”,中国准备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1988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宣布了中国关于中东事务的“五点主张”,其中包括促进对话与和平谈判、要求以色列撤出所有被占阿拉伯领土以换取安全保证,以及最重要的——有关推动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相互承认等内容。尽管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以不同的名义宣布了各自关于中东事务的主张,但钱其琛“五点主张”的核心———通过对话推动巴以两国方案——始终是1988年至今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变的外交立场。
贸易无疑是推动中国对以色列立场转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1985年,为了推动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以色列重新开放了当时已关闭十余年的驻香港总领事馆,并开始通过香港向中国大陆销售其高科技产品,尤其是军事技术和装备。1989年,中美关系短暂的“蜜月期”以不愉快的形式破裂告终后,以色列成为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绕过西方禁运购买先进军事技术的渠道之一。这个特殊渠道对当时的中国至关重要,直到2001年以色列在美国压力下单方面撕毁了与中国的贸易协定为止。
出于对经贸合作的诉求,以及出于认为“阿以冲突”即将彻底结束的判断,中国对与以色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态度日益积极。1990年至1991年间,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与以色列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成为促使中国最终做出这一选择的决定性因素。1992年1月,中国与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也表示了欢迎。《人民日报》称,有了《奥斯陆协议》,巴以和平如今成为了可能。即使在1996年内塔尼亚胡右翼政府严重破坏和平进程的情况下,中国官方媒体仍然相信“《奥斯陆协议》所播下的和平种子,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巴以人民的心田”,并且认为“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会选择支持和平、反对利库德集团的(《中东呼唤和平》,载与《人民日报》,1999年)。1993年10月,即《奥斯陆协议》签署一个月后,伊扎克·拉宾成为首位访华的以色列总理,这表明北京不仅对《奥斯陆协议》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而且确信深化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中国保持与深化自身与巴解组织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障碍。
尽管中国出于对“两国方案”的拥护开始与以色列发展双边关系,但至少在外交辞令上,中国从未动摇过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1988 年 11 月 20 日,在阿拉法特宣布巴勒斯坦国成立五天后,中国正式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于同年 12 月将巴解组织驻北京办事处升格为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1995 年 12 月,中国正式在加沙设立了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大使馆,并于 2004 年 5 月将其迁至拉姆安拉。巴勒斯坦前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一生中曾 14 次应邀访华,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访问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发生在 1980 年之后(他最后一次访华是在 2001 年)。阿拉法特直至去世,都与邓小平以及后来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保持着亲密的私人友谊。
如前所述,自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以来,直至2010年代,中国决策者始终坚信“外交应该服务于经济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服务于外交”,因此,中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主要侧重于贸易,并刻意回避介入中东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正如前中国驻伊朗和阿联酋大使华黎明所言,在这一时期,“中东在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中是被边缘化的地区”(华黎明:2014:8)。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政府有意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国际地位,相应地,中国对包括巴勒斯坦问题在内的中东问题重新产生了政治兴趣。2013年,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分别访问北京时,习近平主席提议促进双方对话,但这一建议遭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忽视。2017年7月,习近平宣布了针对巴勒斯坦冲突的“四点主张”,其核心思想与钱其琛在1988年提出的“五点主张”一致。“四点主张”称中国支持两国方案,支持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此外,它还重申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并要求以色列“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土上的一切定居点活动(《中国代表宣介习近平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四点主张”》2017年)。为宣传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北京方面还于2017年12月主办“巴以和平研讨会”,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总书记艾哈迈德·马吉达拉尼、以色列议会副议长耶希尔·希利克·巴尔等双方主要领导人出席研讨会。
2021年5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再次重申中方有意邀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到北京进行对话。王毅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讲话时不仅强调“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还首次提出“中东不稳,天下难安”。王毅的这番话已成为当今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外交论调的范式。这种将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视为世界和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观点,应当被视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代更广泛的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在当时,中国领导人将巴勒斯坦的反帝斗争视为保护亚洲与非洲战略“后方”免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前线”阵地。然而,与毛泽东时代的立场相反,对“选边站队”的抵触给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外交政策造成了不小的局限性。
应当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在外交辞令上反复承诺自己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对巴勒斯坦国的支持(包括努力争取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并促成巴以和谈——尽管和谈最终失败了),但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和以色列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贸易和投资飞速增长的蜜月期。彼时,由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领土上的活动愈发具有侵略性,再加上以色列对于伊朗核协议的严重敌意,美以关系面临困难。与美国关系碰壁的内塔尼亚胡政府便试图向中国“暗送秋波”。2017年内塔尼亚胡访华时,曾盛赞中以双边关系是“天作之合”,并表示有兴趣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访问期间,中国政府宣布与以色列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但是短短四个月后,巧舌如簧的内塔尼亚胡便故技重施,用同样的“天作之合”比喻来描述以色列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印度的关系。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单方面坚持将包括海法新港在内的中国在以投资项目列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附属项目,但以色列实际上还是拒绝了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倡议。
尽管如此,经济利益——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利益,激发了中国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兴趣。此外,由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2017-2021)期间与中国的恶劣关系,中美之间的大多数沟通渠道被切断,中国也曾寄希望于邀请以色列作为中美继续接触的桥梁。
这一时期,中国在以色列最大的旗舰投资项目是海法新港。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上海国际港务集团(SIPG)与以色列签署协议,获得自2021年起至2025年的海法湾新港运营权。该协议在2018年得到了广泛宣传,至今都被视为“一带一路”在中东的旗舰项目之一。截至2023年,海法新港承运了以色列转运集装箱总量的80%(Lavi 2024)。然而,正如后文即将谈到的那样,中国运营的海法新港项目表面上的繁荣景象很快在加沙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目前正在为高估了中以关系蜜月期的持久性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回顾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一直在毛泽东时代传承下来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原则与自身当前的经济利益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知仍然深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即将巴勒斯坦视为保护亚洲和非洲免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殖民主义前沿;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中东政策本质上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因此中国不愿为了自身与巴勒斯坦的深厚革命友谊放弃与以色列的经贸往来。与巴勒斯坦在政治上的革命团结情谊和与以色列在经贸上的密切联系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造成了日益尖锐的矛盾,而中国则简单地选择了宣称自己是巴以双方共同的朋友,试图将自身塑造为一个置身事外的潜在的调停者的形象。
从1992年到2023年,当国际社会的大环境仍对巴以和平谈判和两国方案抱有希望时,中国成功地在自己的中东外交政策中缓和了这一矛盾,并分别深化了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关系。在中国政府看来,与以色列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既没有成为中国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传统友谊的障碍,也没有使得中国忌惮于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平台上明确表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
然而,近年来,中国作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共同的朋友”的形象愈发难以维持,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这种方针很大程度上建立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巴以和平谈判进程的前提上。由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大肆建立定居点,巴以紧张局势加剧,两国解决方案似乎已经不具备现实操作可能性,中国对这一二十年前提出的巴以问题解决方案的信心似乎已经与巴以问题的实际情况不符。其次,这种外交政策方针是建立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关系这一特定历史背景、特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彼时中国在该地区的参与非常有限,且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中国当时也并不希望在该地区施加实际的政治影响。然而,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一方面希望通过重塑与巴勒斯坦的历史革命友谊来提升其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的国际声誉;但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从2015年到2023年间迅速增长。因此,中国中东政策中政治议程和经济议程之间的矛盾在过去几年中不可避免地加剧,二十年前制定的外交政策立场已经越来越跟不上国际现实的显著变化,中国游离于巴以之间的这种自我认定的“平衡”、“中肯”立场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为巴以两国所接受。
从21世纪初到2023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和压迫变本加厉。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包括2000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6年开始的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战争;2008-2009年、2012年、2014年和2021年以色列对加沙的数次战争;2018-2019年的巴勒斯坦“回归大游行”示威活动;2021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抗议活动的血腥镇压,以及2023年以色列针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在这些事件中,中国发表了数次外交声明批评以色列的行为,但以色列犯下的反人类暴行始终未对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经贸关系产生任何影响。近二十年来,中国与以色列的经贸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客观事实也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怀疑中国方面自称的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诚意。
中国在巴以政策上政治原则与经贸利益之间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注定会推动中国去重新斟酌自己在巴以问题上外交立场和具体政策的长期可持续性。以色列侵略军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日益变本加厉的暴行迟早会戳破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昙花一现的巴以和平进程给国际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也因此会迫使中国放弃成为巴以双方共同朋友这一已经不再切合实际的政治站位和外交目标。以色列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以来,上文所提到的中国外交政策在巴以问题上矛盾已经变得前所未有得尖锐——以色列方面以绑架中国在以投资相威胁,企图逼迫中国放弃对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外交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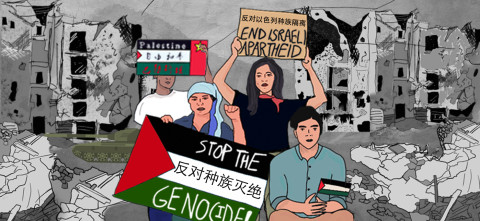
Illustration by Fourate Chahal El Rekaby
中以外交交锋、以色列企图操纵中国民意的尝试、与中国反帝国主义民意的有机构建:中国社会如何看待加沙的种族灭绝
2015年至2020年间,看似一片光明的中以双边关系一度在中国和以色列社会中引发了一些呼吁两国深化战略合作的声音。然而,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武装袭击事件,尤其是以色列随后一年多来对加沙地带进行的大肆轰炸,无可挽回地摧毁了中以两国继续深化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10月7日事件刚过,以色列政府就言辞激烈地要求中国谴责阿克萨洪水行动并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中国毫不意外地拒绝了这一咄咄逼人的要求。中国政府拒绝盲从西方和以色列企图将10月7日事件描绘为“巴以冲突历史开端”的错误叙事。相反,中国将其视为英国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中的无数悲剧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统上是建立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游击战争、以及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武装斗争基础上的革命性人民政权,因此它对全球南方的其他反帝游击武装也始终抱有同情的态度。正如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为第一个全面承认巴解组织的非阿拉伯全球大国一样,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将包括哈马斯在内的任何巴勒斯坦武装抵抗组织列为“恐怖组织”。早在2003年,在那样一个中国社会远比如今更加亲西方且高度依赖从以色列购买高科技和军事装备的时期,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一位中国女记者在采访时任哈马斯领导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时,就已经刻意避免将哈马斯称为“恐怖组织”。2016年,在现任政府的领导下,这种政治考量倾向则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被制度化:新华社明文规定所有中国媒体“不要将哈马斯称为恐怖组织或极端组织。”(《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 2016)。
没有任何文件比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前中国驻苏丹大使马新民先生于 2024 年 2 月 22 日在国际法院 (ICJ) 发表的声明更能直观地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承认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有权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方式抵抗侵略与压迫的官方立场。在海牙的公开听证会上,马新民明确表示:
巴以冲突源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长期占领,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长期压迫。巴勒斯坦人民对抗以色列压迫的斗争,以及他们争取在被占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斗争,本质上是为了恢复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正义行动。(马新民,2024)。
马新民援引多项国际法条款,表示“人民发起的斗争,按照国际法中解放自决权利的原则,包括反对殖民占领,外国势力入侵和统治的武装斗争,不应被视为恐怖行为。”并且“与此相关的武装斗争与恐怖主义行为是有区别的,这是国际法赋予的,两者的区别得到了若干国际公约的承认。”他进一步表示:“出于对民族自决权的追求,巴勒斯坦人民用武力反抗外国压迫,并完成独立建国,是国际法确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马新民,2024)。
马新民在海牙的声明是中国政府当前关于巴勒斯坦武装斗争和抵抗组织立场最明确且最具代表性的诸多文件之一。早在2023年10月,中国就开始通过一系列支持巴勒斯坦的公开声明反复呼吁以色列立即停火,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投票声援巴勒斯坦。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向世界证明,它没有抛弃它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外交传统,也没有抛弃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锻造的中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同志情谊。尽管中国并未表态它将会通过正式加入“抵制、撤资和制裁”(BDS)运动的方式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尽管中国至今尚未在官方外交文件中直接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定义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罪行,但中国至少已经向世界证明,它不愿意像西方(尤其是是美国和德国)那样对这场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保持沉默或充当以色列的帮凶。
自2023年10月起,中国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多次对以色列杀害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的行径表示强烈批评,来自以色列当局的强烈反对和外交压力并未使中国改变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也并没有放弃促进对话的固有信念。由于在当前形势下显然不可能促进巴以之间的直接对话,中国外交部便转而试图促进巴勒斯坦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对话。2024年3月17日,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王克俭大使会见了时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伊斯梅尔·哈尼亚。媒体没有披露此次会晤的具体情况,但很可能正是在这次会晤中,王克俭向哈马斯外交官发出了访华的官方正式邀请。因为不到一个月后,哈马斯代表就抵达北京与法塔赫代表进行谈判。外界并不清楚四月份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由于双方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这次会议的结果很可能并不理想。
然而三个月后,以法塔赫和哈马斯代表为首的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在2024年7月23日于北京开始了新一轮谈判,并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见证下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即《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声明指出,各派将共同合作,“建立一个致力于加沙冲突后重建的临时民族共识政府”(《巴勒斯坦各派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2024年)。
诚然,《北京宣言》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它无法真正实现巴勒斯坦的团结,也无法阻止加沙持续不断的战火。但值得进行对比的是,就在《北京宣言》闭幕式后的第二天,太平洋彼岸出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无耻的历史时刻之一:2024年7月24日,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发表了长达56分钟的演讲,赢得了无数议员的起立喝彩和掌声,令世界震惊的是,平日里自诩在乎人权的美国国会竟然如此赤裸裸地公然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罪行。
不出所料的是,中国对巴勒斯坦的外交支持招致了以色列方面歇斯底里的反对。早在10月中旬,以色列外交部就多次对中国拒绝谴责阿克萨洪水行动表示不满和愤怒。在双边外交渠道、公开声明和联合国会议上,中以外交官多次展开激烈交锋。
以色列还以中国承包的海法新港作威胁,试图向中国施压。自 2023 年 10 月起,由于战争带来的安全风险,运营该港口的中国公司大幅减少了贸易量,并在 2024 年 1 月红海危机后完全停止了运营。此事很快被以色列主流媒体 Ynet刻意进行政治方面的扭曲渲染,Ynet上纲上线地宣称该中国公司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主动切断与以色列港口贸易关系的公司”(Azulay 2024)。2024 年 1 月,以色列国营的阿什杜德港董事长要求以色列政府终止中国承包海法新港的资格,给出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拒绝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与Ynet报道口径类似,此人也抱有对以色列“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蛮横逻辑,污蔑中国企业碍于安全形势而减少对以贸易的做法相当于在客观上参与了对以色列的“海上禁运”(Rabinovitch and Saul 2024)。
时至今日,以色列政府仍未正式撕毁与中国就海法湾新港口项目达成的25年协议。然而,考虑到过去一年中以两国外交关系的日益紧张的外交背景,以及海法港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黎巴嫩真主党袭击目标这一地理因素,可以说这项规模宏大的投资充满了来自以色列以及域内反以武装力量同时施加的地缘政治风险,堪称前途多舛。可以说,该项目恐怕是“一带一路”倡议迄今为止在中东地区投资中最大的失误,其原因在于投资者过于拘泥于片面的经济考量,却在中以关系蜜月期的背景下被以色列方面单方面的宣传说辞蒙蔽了判断、忽视了该项目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
除施加外交压力、威胁关闭海法港外,以色列还在中国网络平台上发起了大规模政治宣传活动,妄图操纵中国社会的舆论民意。
2023年10月8日,即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后的第二天,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在微博(一个类似于X的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官方账号以及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微博账号开始同时密集发文,强调此次袭击中被绑架的人质之一诺亚·阿加马尼(Noa Argamani)有一半中国血统。为了进一步煽动中国网民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挑动中国民众反对政府的官方立场,以色列大使馆还故意散布虚假信息,谎称阿加马尼出生于北京。11 事后根据阿加马尼的母亲李春红(以色列名字是利奥拉·阿加马尼)的澄清说法来看,阿加马尼出生于北京的说法完全是以色列大使馆编造的虚假信息。为响应以色列大使馆的呼吁,微博上一时间出现了大量亲以色列言论,其中很多帖子的发布者具有明显的“僵尸号”特征,这些账号呼应以色列大使馆的说法大肆传播所谓阿加马尼是中国人、甚至中国公民的谣言。从 10 月 9 日到 12 月 26 日,以色列驻成都领事馆从未停止过一遍遍强调阿尔加马尼的中国血统,并且用大打感情牌的方式企图挑拨中国民众的情绪、煽动中国网民反对政府的外交立场。例如,10 月 26 日的帖子就将内塔尼亚胡描绘成一位心软善感、见不得百姓受苦的大善人,说他听到阿加马尼的母亲李春红身患癌症却见不到女儿的消息就心碎难过,因此焦虑地决定直接“越过外交礼节和规则,请求中国驻以色列大使直接传达请求。” 12 实际上,该政治宣传就是企图通过大打感情牌的方式挑拨民众质疑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企图用民意绑架政府的外交政策。
虽然以色列大使馆的宣传攻势未能赢得大多数中国网民的支持,但在一段时间内确实对中国政府造成了相当大的公众压力。自2011年以来,在国外爆发危机期间保护和撤离海外中国侨民一直是中国政府在内宣议程中重点强调的内容,因此,如果中国公民被一个中国不愿谴责的武装实体扣为人质,这将损害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公信力。此外,中国政府通常倾向于通过专业的双边外交渠道处理此类问题,而非公开报道外交问题的细节,但以色列的操纵民意的宣传攻势则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直接通过公开渠道回应此事,使得中国政府一时陷入被动。讽刺的是,以色列这种企图煽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反对官方外交政策的行为,很快就遭到了来自它所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噬:在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及她和她的女儿是否是中国公民时,李春红以相当傲慢的语气斥责中国网民:“我现在是以色列国籍,难道说是以色列国籍,你们中国人就不可以帮助我吗?我觉得帮助人,就是人人的义务。你听懂了吗?”(李春红访谈,2023年)“你们中国人”这一枉顾丝毫同胞情谊的表述的使用引发了中国网民的极大愤怒,舆论哗然,以色列方面企图以阿加马尼的中国血统作为突破口煽动民意绑架中国外交政策的计划就此宣告流产。
除了通过传播虚假信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企图绑架中国外交政策,以色列驻华大使馆还尝试了各种其他形式的网络宣传手段。最常用的策略就是以咄咄逼人的态度公开批评中国的外交立场,并在微博上宣传以色列的叙事。例如,10月14日,以色列驻华大使馆不仅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立场“深表失望”,还颐指气使地指责中国外交部提及加沙大量平民伤亡的说法是“与过去几天发生的悲剧和恐惧不符且不实”的虚假信息。13 时至今日,以色列账号仍在持续不断地发表此类帖子。
除了散布虚假信息和公开指责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之外,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还积极传播亲以色列的信息。例如,以色列经常用典型的“殖民女权主义”论调粉饰洗白自身,称自己是该地区唯一“文明”且“对女性友好”的国家。在2024年国际妇女节当天,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就曾组织了一场网络研讨会,将妇女权利与10月7日的袭击事件联系起来,企图进一步煽动中国民众尤其是女性群体反对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外交政策立场。 14
以色列大使馆还积极与其在中国知识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言人合作,利用这些公众人物来传播虚假信息、粉饰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罪行。此类宣传中最典型也最令人惊诧的例子是曾担任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一职的老一辈权威学者殷罡的争议性言论。面对加沙惨绝人寰的悲剧,殷罡却在电视上表示中国民众应该“冷眼看中东”,指责巴勒斯坦人“专在中东卖眼泪”。殷罡在镜头前公开传播粉饰以色列战争罪行的虚假信息,声称“前不久浸信会医院挨炸,哈马斯公布死了五百人,我经过仔细调查,一个人没死”。在同一个采访中,他还讥讽中国民众,“你别听说加沙又死了一万多老百姓你就掉眼泪,也许后面应该去掉一个零。你不要动情绪,看的是事实,咱们就说事儿。”( 《中东不谈眼泪——专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殷罡》,2023 年)。八个月后,因粉饰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断受到中国网民猛烈批判攻击,堪称晚节不保的殷罡突发心脏病去世。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随即发表声明,称殷罡是“一直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中东问题的发展和地区重大事件”的“老朋友”。 15 以色列大使馆这篇悼词则被许多中国网民视为证明殷罡与以色列政府长期存在深度利益往来勾连的证据,更加证明了殷罡此前关于加沙战争的令人咋舌的错误言论并不是严肃客观的学术观点,而是一边倒的亲以色列政治宣传。
回顾以色列驻华大使馆自2023年10月以来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读者不禁要问:那么,这场宣传攻势是否成功赢得了大多数中国青年对以色列的好感乃至支持呢?答案是决然否定的。自10月7日以来,中国网民对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反殖民斗争,包括武装斗争,表达了压倒性的支持。许多中国年轻网民用极具诗意的语言将参加阿克萨洪水行动的巴勒斯坦伞兵武装部队称为“蒲公英战士”,原因有二:其一,在空中飞舞的降落伞看起来就像随风飘扬的蒲公英种子;其二,蒲公英种子在落地后可以随处生根发芽,这种植物的生命力与韧性正与巴勒斯坦人民七十七年来流离失所却始终不忘故国、坚定斗争的顽强生命力与坚韧民族性如出一辙。
在中国年轻网民最为活跃的视频分享网站“哔哩哔哩”上,有很多中国网民为纪念“蒲公英战士”而制作的视频。一些最受欢迎的视频(每个视频的观看次数在50万次以上)标题极为优美而富有诗意,具有强大的情感感染力:“妈妈,我化作蒲公英回到故乡了!”;“蒲公英不会死亡,它只是飘向更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故乡。”;“曾经废墟中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化成了蒲公英,飘向了他们祖祖辈辈思念的故乡。” 16
过去的一年内,中国网民对深入巴勒斯坦的历史与时事进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抖音上随处可见加沙战争的画面,许多网络内容创作者致力于制作视频,向观众介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运动的历史,或介绍战争的最新进展。还有一些人专门将巴勒斯坦抵抗武装所发布的视频搬运到中国互联网上,并为观众进行深度分析。17 叶海亚·辛瓦尔战死后,甚至有中国网络内容创作者主动将其小说《荆棘与康乃馨》翻译成中文以示纪念。 18
与此同时,无数中国网民通过微博联系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试图为巴勒斯坦民众捐款。相反,以色列驻华使领馆的微博评论区内却充斥着无数充满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的批判性评论。这些批评的声音使得以色列政府企图扭曲中国群众对于加沙种族灭绝战争认知的宣传努力化为泡影。讽刺的是,这个号称“中东唯一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权居然无法容忍中国网民民主地表达自身对于巴以问题的观点:自2023年10月起,以色列驻华使领馆关闭了微博评论区,只允许显示亲以色列的所谓“精选评论”。相比之下,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账号下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不友好的声音,但巴勒斯坦驻华大使馆却从未像“中东唯一一个民主国家”那样关闭评论区或开启“精选评论”模式以打压中国网民的民意与质疑声。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美国国务院禁止将以色列的政策与纳粹德国的政策相提并论,称这种比较定性为所谓“反犹主义”(“Defining Antisemitism”,2016),但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主义扩张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人民却情不自禁地将加沙种族灭绝战争与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对中国平民的大屠杀相提并论。事实上,中国人民自身饱受侵略的历史创伤正是他们对巴勒斯坦人民天然抱有亲切感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网民常说“中国的昨天就是巴勒斯坦的今天”或“巴勒斯坦就像百年前的我们”;中国网民也喜欢称呼巴勒斯坦抵抗战士为“老乡”,而“老乡”在历史上也广泛被用来称呼二战期间的中国抗日游击队员。就连美国官方宣传喉舌“美国之音”(VOA)在一篇关于中国网民所谓“反犹主义”的报道中也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承认,许多中国人认为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一支奋力抵抗日本殖民侵略军十四年直至最终胜利的中国游击队)非常相似((Ma Wenhao,2023年)。2023年10月24日,忠心护主的德国驻华大使馆发表了一份枉顾基本外交礼仪、粗俗野蛮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外交声明,将所有把以色列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的中国人称为“不是无知的蠢货,就是无耻的混蛋”。19 然而,以色列、德国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很快发现,他们挑衅式的傲慢态度给他们的微博评论区招致了来自更多中国网友的愤怒批评,中国网民也继续坚持将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战争罪行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进行比较。
有趣的是,尽管中国政府从未在官方声明或政府文件中直接采用过这种比较,但它曾暗中表达过对这种比较的默许和同情。比如,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播出了对巴勒斯坦驻华大使法里兹·马赫达维阁下的采访。马赫达维大使在采访中就将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民与二战期间在日本占领下饱受苦难、惨遭屠杀的南京市民进行了比较(《巴勒斯坦驻华大使:你不懂这种痛苦,因为你出生在自由独立的国家》 2023)。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薛剑先生甚至在其官方推特账户上分享了中国年轻画家周蛇吉创作的漫画,该漫画生动地将以色列士兵与二战期间屠杀中国儿童的日本法西斯分子进行了比较,斥责两支军队在杀害平民儿童方面堪称一丘之貉。 20

Illustration by Fourate Chahal El Rekaby
从历史的惯性到有机的团结:在中国青年对加沙的讨论中管窥中巴未来团结的希望
回顾当代中国对巴勒斯坦的外交政策立场,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不同遗产之间的断层与张力:第一种遗产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思想和反帝国主义精神,正是毛泽东思想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层支援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实践遗产确保了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始终是中国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正确原则。第二种遗产则是改革开放后的“平衡方针”,这种方针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已经制度化,它使得中国政府认为中以关系既不构成对中巴关系的威胁,也不构成中国支持“两国方案”的障碍。
在包括但不限于巴以冲突在内的各种深刻的政治课题上,中国现政府都不愿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遗产和改开之后的历史遗产之间选边站队,而是强调不能用前三十年去否认后四十年,也不能用后四十年去否定前三十年,试图通过搁置差异、强调共同点的方式来简单地忽略两种路线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中国对正眼下在发生的加沙种族灭绝事件的反应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所有国际平台上都明确反对以色列,而且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使用一切可用手段(包括武装斗争)来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当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大国都忙于通过将社会中亲巴勒斯坦的声音定性为“反犹太主义”来对其进行政治迫害与打压时,中国政府包容,甚至一定程度上鼓励和配合了中国网民表达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朴素而真诚的正义感。
然而,中国近二十年来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似乎更多受到毛泽东时代历史惯性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全球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最新发展。如前文所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承认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并曾是全球声援巴勒斯坦运动的先锋旗手。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尽管中国与巴解组织的历史友谊依然存在,但中国政府对诸如BDS运动在内的全球声援巴勒斯坦运动新趋势、新平台、新网络却相当疏远,甚至不甚了解。中国学界、媒体界也未能与巴勒斯坦境内或巴勒斯坦海外侨民知识分子智识界之间建立富有成效的“三轨外交”声援交流网络。
由于缺乏对当地矛盾的深入了解且不愿将自身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置于风险之中,中国政府不愿接受“两国方案”越来越不具备可行性这个苦涩的现实,也不愿接受在巴勒斯坦人面临愈发严峻的生存威胁这一现实背景下,中国希望成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共同的朋友这一目标也越来越不具备可行性的事实。面对加沙持续不断的种族灭绝,中国政府努力在外交平台上支持巴勒斯坦,但还没有意识到正式采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定义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必要性。中国官方支持南非在国际法院对以色列种族灭绝的指控,但并未在其外交文件中直接使用这一概念。
此外,中国政府过于热衷于利用自身在北京的外交平台推动巴以双方之间的和谈对话,以其提升中国的全球声誉和软实力,但没有充分意识到,像南非那样通过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法律平台对以色列提出指控,实际上可能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欧美左翼面前提升中国国际声望的最佳途径。令人同样感到遗憾的是中国政府对BDS运动知之甚少,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关于中国或中国学术机构加入BDS运动可能性的讨论。
此外,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也可能使得中国除了发表外交声明和举办对话活动外,无法在支持巴勒斯坦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如前所述,北京方面知道特朗普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并曾有意在特朗普第一的任期内将以色列作为中美沟通的潜在桥梁。考虑到北京与以色列的蜜月期已在去年以外交冲突的形式告终,北京方面可能已经放弃了邀请以色列作为中美关系中间人的这一幻想。然而,特朗普强烈的亲以色列立场也会阻止北京在经贸方面对以色列采取强硬措施。考虑到中国对 2017 年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反应,可以预期中国在未来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一方面,中国将以特朗普对以色列战争罪行的盲目支持为契机,发表更多支持巴勒斯坦的外交声明和举行更多对话谈判,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将确保不介入巴勒斯坦或黎巴嫩的武装斗争,不介入任何针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运动,以避免给本就低迷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国在国际声援巴勒斯坦运动中未来的角色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在国家层面,以色列政府自2023年10月以来歇斯底里的态度已经让中国政府感到不满。中国拒绝谴责阿克萨洪水行动,以及与以色列在联合国的交锋,也已经终结了两国之间此前的蜜月期。尽管未来中以经济联系可能会继续深化,但在海法新港纠纷之后,两国未来可能不会再愿意在类似的大型项目上合作。
在社会文化方面,加沙战争促使日益反西方的中国青年群体重新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遗产建立精神联系。通过积极地运用网络资源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当前形势,并热情地创作诗歌、歌曲、视频、绘画以及其他以赞扬巴勒斯坦人抵抗以色列侵略占领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当代中国青年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被当前惨绝人寰的加沙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围绕这场战争所爆发的全球声援巴勒斯坦浪潮所塑造的。因此,这一代中国青年很可能会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锡安主义叙事最持有批判性态度的一代人。从长远视角来看,这一代青年人终将在未来的中国政府和社会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的职位,也因此,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的中国重新拥抱其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反殖民传统,并在全球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笔者想援引作家张承志先生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张承志是一位具有传奇人生经历的中国回族作家。他在中学时期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运动,据说他还是“红卫兵”一词的最早发明者。他后来的职业生涯则致力于为中国读者撰写有关巴勒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文章。在他的著名文章《赤军的女儿》中,他以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纪念了一群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远赴中东、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合作参与到巴勒斯坦武装斗争当中的日本毛主义者。张承志用极富诗意的文字留下了他对于未来世界前景的预言:
锲而不舍否定革命的工程,是注定徒劳的。因为控制、压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这一切都会推动思考,使人们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选择革命。 (张承志 2009).
今天,来自巴勒斯坦的蒲公英种子伴随着呼唤自由与解放的风潮漂荡在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跨越千山万水降落在无数中国青年的心田。这些正在迅速生根发芽的种子必将突破西方叙事霸权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最终激励中国青年去重新思考当代中国在全球反帝事业中的角色,并重新拥抱他们的阿拉伯兄弟姐妹们。
本文仅反映作者本人观点,并不一定反映 TNI 的观点或立场。
参考文献
Abu Salma. Zuguo song祖国颂 [Songs for the Motherland], translated by Yang Xiaobai杨
孝柏. Beijing: zuojia chubanshe作家出版社, 1964.
An, Huihou安惠侯. “Aiji yu xinzhongguo jianjiao shimo埃及与新中国建交始末 [The
Road to Sino-Egypt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rab World Studies vi (2008), 4. “Anti-Israel Resolution Adopted at Bandung; Red China Supports Arabs,”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22 April 1955.
Azulay, Yuval. “China Halts Shipments to Israel, Hurting its Own Port,” Ynet News. January
16th 2024. https://www.ynetnews.com/business/article/r1wxe0gkp
Balesitan renmin bisheng 巴勒斯坦人民必胜 [The Palestinian People Will Win]. Produced
by the Central Studio of News Reels Production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May, 1971. Film.
Balesitan zhandou shiji 巴勒斯坦战斗诗集 [Battle Poems of Palestine].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
“Balesitan zhuhua dashi: nibudong zhezhong tongku, yinwei ni chusheng zai ziyou duli de
guojia巴勒斯坦驻华大使:“你不懂这种痛苦,因为你出生在自由独立的国家”[Palestinian Ambassador to China: You Do Not Understand This Kind of Suffering Because You Are Born in a Free and Independent Country]”, China Daily, 24 October, 2023. https://b23.tv/pLVOv4F
“Buxv fanghuo, buxv qinlue 不许放火,不许侵略 [No Instigation, No Invasion]”, People’s
Daily, 1 November 1956.
Cooley, John K. “China and the Palestinian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1972), 20,
doi:10.2307/2535952, accessed 27 Nov. 2020.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Xingshi poshi women jinyibu gaige kaifang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Current Situation Demands Us to Push for Furth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excerpts from Deng Xiaoping’s Conservation with Ethiopian President Mengistu on 22 June, 1988, in Volume 3 of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邓小平文选. Accessed on official website of CPC party-media Qiushi 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books/2019-07/31/c_1119485398_88.htm
“Defining Antisemitism,”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6.
https://www.state.gov/defining-antisemitism/
“Gongzuo fangfa liushi tiao 工作方法六十条 [Sixty Points of Working Methods]”, Jianguo
yilai zhongyao lishi wenxian bianxuan建国以来重要历史文献选编 [The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Archiv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the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Centr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vol. 11, 1995.
Guoji guanxi yanjiuyuan国际关系研究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Zhongdong
wenti wenjian huibian 中东問題文件彙編 [A Collection of Reference Materials on Middle Eastern Affairs] (Beijing: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8), 278.
Harris, Lillian Craig.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New York: Tauris, 1993).
Hua, Liming 华黎明. “Yilang hewenti yu zhongguo zhongdong waijiao 伊朗核问题与中国
中东外交 [The Iran Nuclear Issue and China’s Middle East Diplomacy].”阿拉伯世界研究Arab World Studies, no. 6, November 2014:4-16.
Lin, Biao林彪. “Long Live the Victory of People’s War”, Peking Review, xxxvi (1965), 22.
“Jianjue zhichi aiji he xuliya kangji yiselie de junshi qinlue坚决支持埃及和叙利亚 抗击以
色列的军事侵略[Firmly Support Egypt and Syria in Resisting Israeli Military Aggression]”, People’s Daily, 8 October 1973.
Mao, Zedong毛泽东. “People of the World, Unite and Defeat the U.S. Aggressors and All
Their Running Dogs”. It can be accessed on 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s,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selected-works/volume-9/mswv9_86.htm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ijing, February 18, 1973, 2:43–7:15 p.m.,” 18 February
197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XVII, Vol. XIII, China 1973–1976.
“Sugong lingdao tong women fenqi de youlai yu fazhan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
展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Soviet Communist Party Leaders and Us]”, Jianguo yilai zhongyao lishi wenxian bianxuan建国以来重要历史文献选编 [The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Archiv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the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Centra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vol. 17, 1997.
Shai, Aron. China and Israel: Chinese, Jews; Beijing, Jerusalem (1890–2018). Boston: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9.
Shichor, Yitzhak.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hindler, Colin. Israel and the World Powers (London: I. B. Tauris & Company, 2014).
“Palestinian Factions Sign Beijing Declaration on Ending Division and Strengthening
Palestinian National Unity,” 23 July 2024. Accessed on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www.mfa.gov.cn/eng/wjbzhd/202407/t20240723_11458790.html
Rabinovitch, Ari, and Jonathan Saul. “Israel's Ashdod Port Sees Strategic Risk from China
during Gaza war,” Reuters, 26 January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sraels-ashdod-port-sees-strategic-risk-c…
Interview of Li Chunhong by IFeng News on 13 October, 202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6w411r7gf?vd_source=09e817274905aa2d416b451efc22f697&spm_id_from=333.788.videopod.episodes
“Let’s Not Talk about the Tears in the Middle East: An Interview of Research Fellow Yin
Gang from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Academy,” IFeng News, 13 November, 2023.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j411E7rs/?spm_id_from=333.337.search…
Ma, Xinmin 马新民. Statement at the “Legal Consequences arising from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Israel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including East Jerusalem – Public hearings,” 22 February, 2024. Accessed on the official media of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https://www.icj-cij.org/multimedia/203577
Ma, Wenhao. “Chinese Vloggers Glorify Hamas with Cosplay and Posts,” Voice of America,
19 December, 2023. https://www.voanews.com/a/chinese-vloggers-glorify-hamas-with-cosplay-a…
Xu, Min 徐敏, Balesitan wenti zhenxiang 巴勒斯坦问题真相 [Truth of the Palestinian
Issue] (Manchuria: Xinhua shudian dongbei zong fendian 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 1950).
Institute on the Religion of Islam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
所, Balesitan wenti lishi gaikuang巴勒斯坦问题历史概况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alestinian Issue] (Shaanxi: Shaanxi renmin chubanshe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73).
Workers Theoretician Group of the Wuhan Heavy Duty Machine Tool Factory武汉重型机床
厂五一车间工人理论组and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Balesitan wenti de youlai he fazhan 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lestinian Issue]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人民出版社, 1976).
Xiao yingxiong Kasaimu小英雄卡塞姆 [Little Hero Qassam], Painted by Liu Renyi 刘仁
毅.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2.
Xiao yingxiong Kasaimu小英雄卡塞姆 [Little Hero Qassam], Poem written by Hong Tie
红铁,Painted by Shuo Fang朔方. Harbin: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3.
“Xinhuashe xinwen xinxi baodao zhong de jinyongci he shenyongci 2016 nian 7 yue
xiuding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6年7月修订) [Words That
Are Forbidden to Use and Words That Should Be Used Only With Caution in the News Report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 The Edition of July 2016]. 2019.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September 16th.
https://www.cup.edu.cn/yww/gfbz/9311271.htm
“Yigongzhuzhang caiqu duli heping he zhongli zhengce 以共主张采取独立、和平和中立政
策 [Israeli Communist Party Advocates for Independent, Peaceful, and Neutral Policy]”, People’s Daily, 19 March 1956.
“Yiselie afuhan fenlan jue yu woguo jian waijiaoguanxi zhou waizhang fenbie fudian biaoshi
huanying 以色列、阿富汗、芬兰决与我国建外交关系 周外长分别复电表示欢迎 [Israel, Afghanistan, and Finland Decided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 with Our Country, Foreign Minister Zhou Replied to Each of Them and Expressed Welcoming]”, People’s Daily, 17 January 1950.
“Yiselie renmin buyuan wei yingfamei huozhongquli, yigong qianze diguozhuyi Shandong
dui aiji d junshi maoxian yinmou以色列人民不愿为英美法火中取栗 以共谴责帝国主义煽动对埃及的军事冒险阴谋[Israeli People Do Not Want to Risk Themselves for Britain, U.S., and France – ICP Condemns Imperialist Instigation for Military Adventurist Conspiracy against Egypt]”, People’s Daily, 16 September 1956.
“Zaianlihui taolun suowei zai zhongdong jindu tinghuo wenti de huiyi shang Qiao
Guanhuatuanzhang jielu sumei tuixing qiangquanzhengzhi wannong pianjv在安理会讨论所谓在中东监督停火问题的会议上 乔冠华团长揭露苏美推行强权政治玩弄骗局[At the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to Discuss the So-called Ceasefire Supervision Issue in the Middle East, Chief Delegate Qiao Guanhua Exposed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wer Politics and Manipulative Scaming]”, People’s Daily, 25 October 1973.
Zhanqi piaopiao 战旗飘飘 [The Waving Flag of Combat].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1.
Zhang, Chengzhi. “Chijun de nuer 赤军的女儿 [Daughter of the Japanese Red Army],” in
Jingzhong yu xibie: zhi riben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Respect and Farewell: To Japan]. (Beijing: Zhongguo youyi chubanshe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 Also accessible online at: https://www.mzfxw.com/m/show2.php?classid=13&id=166796
“Zhongdong huhuan heping 中东呼唤和平”[The Middle East Calls for Peace]”, People’s
Daily, 21 May 1999.
“Zhongguo daibiao xuanjie Xi Jinping guanyu jiejue balesitan wenti sidian zhuzhang中国
代表宣介习近平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四点主张”[Chinese Representative to U.N. Announces and Introduces Xi Jinping’s Four-Point Propositions on Solving the Palestinian Issue]”, People’s Daily, 27 July 2017.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727/c1002-29430754.html